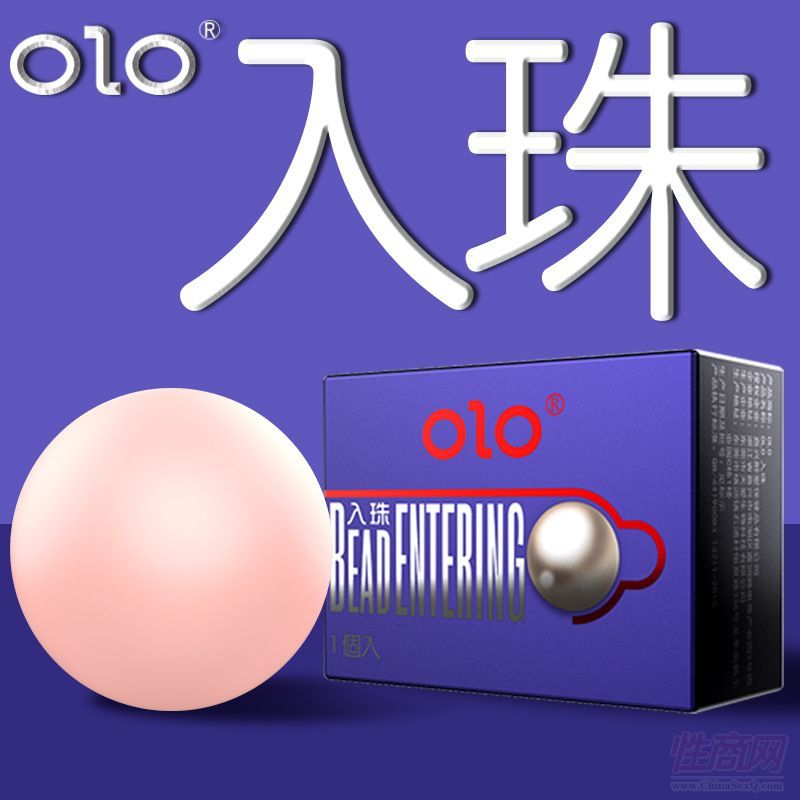艾滋病日,安全套的两副“面孔”



2010年10月27日,798艺术区,安全套创意展上,所有的模特头上都戴了安全帽。郭晓飞 学者
安全套广告
在“妨碍了道德”和“妨碍了防艾”之间
一个人使用安全套来保护自己和他人免于身体伤害,另一个人完全无视这样的伤害,哪一个更加维护了公共秩序和善良风尚?
各个国家的防艾历史都显示,安全套是阻断涉性艾滋传播的不二利器,无论是民间的防艾组织,还是国家决策层,在这一点上达到了高度的共识。国务院制定的《艾滋病防治条例》和下发的《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都强调了要积极推广安全套。
然而,现实是,我们在所谓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媒体上鲜有见到对安全套的推广使用,而且越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媒体,也就是受众越广泛的强势媒体,如电视屏幕上,对安全套的正面推广几乎处于绝缘状态。1999年11月28日,国家计生部门在中央电视台《中国人口》栏目播出一则公益广告,宣传安全套可以有效预防艾滋病,但只播了1天便被停播。
一般认为,安全套推广之法律法规上的障碍是1989年10月13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关于严禁刊播有关性生活产品广告的规定:“近来,一些地区出现了有关性生活产品的广告,如‘夫妻运动快乐器’、‘真空性生活补助器’等。广告中称这类产品是治疗性功能障碍,辅助性生活的医疗器械。这类产品向社会宣传,有悖于我国的社会习俗和道德观念。因此,无论这类产品是否允许生产,在广告宣传上都应当严格禁止。”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广告法》第七条第五款所禁止的广告中有“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和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内容。
支持安全套推广的学者认为这些禁令已经过时了,关于性的道德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不应因循守旧,甚至从解释技术上着眼,认为安全套不是为了满足性生活的需要,而是防病和防孕的工具,所以不适用上述禁令。
而在我们国家,作为避孕的工具,安全套早已在计划生育国策的框架下获得了正当性。社会中大量非计划的怀孕、堕胎,都使得女性的身体深受其害,让人怀疑主流社会对安全套的排斥是男权社会事不关己的漠然。同样的道理,性工作者、男同性恋人群,作为艾滋的易感人群,也处在社会的边缘状态,对于他们健康状态的漠视,是否也可以解释主流对安全套推广的无所谓。
说起公共秩序和善良风尚都过于抽象而难于讨论,不妨问一个问题:一个人使用安全套来保护自己和他人免于身体伤害,另一个人完全无视这样的伤害,哪一个更加维护了公共秩序和善良风尚?
安全套证据
在“打击卖淫嫖娼”还是“鼓励预防艾滋”之间
一方面遵守推广安全套的倡导性规定难以落实,另一方面,违反“避免将避孕套作为卖淫佐证报道”的现象屡屡出现,容易抵消推广安全套的成果。
在一次全球基金资助的防艾小组能力建设培训会上,我问了这么一个问题:大家在电视上见到过安全套吗?大家都摇头说没有,我说我见过,而且还见过不少。电视并没有对安全套进行符号性灭绝,而是有选择地呈现。在打击卖淫嫖娼的新闻报道中,一定会有一个镜头,一个大特写,一堆散乱的安全套。纸媒的报道中也充斥着这样的话语:“一美发厅内查获大量安全套”,“并在房间垃圾桶里查出了大量的作案工具”,“缴获大量避孕套”。这里提出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其一,安全套是否可以作为卖淫嫖娼的证据?
上世纪90年代一个段子广为流传,警方在小姐的包里面查到三样东西,口红、《文化苦旅》、安全套。安全套作为卖淫嫖娼的证据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发生这样的新闻:丽水一公务员被警方施以卖淫嫖娼行政处罚后,将警方告上法庭,律师辩护道:“警方连关键的物证安全套都没有找到”。对于卖淫嫖娼的认定,安全套有证明力吗?2001年公安部下发了《关于对同性之间以钱财为媒介的性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第一次比较清晰地界定了卖淫嫖娼的概念:“不特定的异性之间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包括口淫、手淫、鸡奸等行为,都属于卖淫嫖娼行为,对行为人应当依法处理。”根据这样的概念我们可以知道,对于卖淫嫖娼的界定来说:安全套的出现既非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在网上相约一夜情,安全套能证明他们的关系是以财务和金钱为媒介吗?
这些年来,因为预防艾滋议题的发酵,时有传言说警方将不会在打击卖淫嫖娼的时候把安全套作为证据使用。一直致力于艾滋防治的组织北京爱知行研究所2008年12月1日曾致信公安部,要求对“公安部关于安全套不得作为卖淫嫖娼证据的法规、规章”进行信息公开。2008年12月22日,公安部政府信息公开办公室做出答复,表示公安部从未发布过安全套不得作为卖淫嫖娼证据的规范性文件。事实上,公安部也从没有出台过要把安全套作为卖淫嫖娼证据的文件或规定,但是警方可能把它作为证据链环中的一个辅助证据向当事人施加心理压力。
其二,一些媒体大肆渲染安全套作为卖淫嫖娼证据是否妥当?
虽然公安部没有明文规定安全套不能作为卖淫嫖娼证据,可是相关部门却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媒体大肆渲染安全套作为卖淫嫖娼证据。1998年包括中宣部等在内的九部委共同发布的《预防艾滋病性病宣传教育原则》(卫疾控发[1998]第1号)中指出:推广使用避孕套预防性病艾滋病传播的宣传,要避免将避孕套作为卖淫佐证的报道。
中国政府在预防艾滋的问题上表现出了难得的实用主义理性,清洁针具的交换、毒品上瘾的美沙酮替代、娱乐场所百分之百安全套项目的推行,都在道德高调和务实策略间做出明智选择。在道德风化和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危险之间,我们不难两害相权取其轻。
然而,一方面遵守推广安全套的倡导性规定难以落实,另一方面,一些媒体违反“避免将避孕套作为卖淫佐证报道”的现象屡屡出现,容易从正反两面抵消防艾组织推广安全套的成果。
安全套形象
在“好得很”和“糟得很”之间
我一直想做一个纪录片,题目就叫“安全套的两副面孔”。让公众知道安全套广告付诸阙如,哪怕是公益的,也容易得到“遭得很”的道德污名。
全国各地成立了很多的防艾小组,作为民间力量对高危人群的行为进行干预,发放安全套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来提高安全套在高危人群中的使用率,对安全套进行“去污名化”的工作,我甚至在一次会议上看到有小组用香囊袋来装安全套,说是要打造“随身带套很吉祥”的“新民俗”。
这些宣传“好得很”的努力一定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个效果遇到了“糟得很”形象的稀释。我一直想做一个纪录片,题目就叫“安全套的两副面孔”。我们可以把电视里面出现的安全套形象做一个记录,要么安全套广告付诸阙如,哪怕是公益的,要么都是卖淫嫖娼证据,“遭得很”的道德污名;作为对比,我们可以拍一些防艾志愿者在高危人群中推广安全套使用的镜头,看他们怎样费尽心机让安全套使用深入人心。
一些媒体大声地、正式地渲染安全套的伤风败俗,而志愿者只是小声地、非正式地宣传安全套的防病保命;传统媒体对公众的导向是“水浇地”,无远弗届,志愿者的努力是“滴水灌溉”,干预覆盖有限。比如,我们不能假定所有的同性恋者都会去酒吧、公园、浴室接受志愿者的安全套意识教育,我们甚至不能假定他们都上网来接受防艾资料,毕竟,我们这个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一定也有数字鸿沟。但是这个局限却不是防艾小组的错误,而是宏观制度有待改进的问题。所以我一直认为,如果媒体不配合、不参与,防艾工作的成效一定会大打折扣。
防艾小组
在“办事员”还是“政策倡导者”之间
不是等这些问题有答案了才遵照实行,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全在于各种力量以切身行动来做出回答。
因为同性恋群体受到艾滋病的威胁,政府主导的防艾活动首先遭遇的问题就是同性恋者在哪里?于是,防艾小组出现的最根本的首要的原因是:寻找同性恋来作为干预对象。
政府主导的防艾始终都很难放弃这样一个定位,以至于各种各样的能力建设都是培训的事务性工作,怎么发套,怎么写项目书,怎么写项目结题报告书,怎么做财务报表。不会培训的是,什么样的公共政策导致了防艾的困难,怎么去做倡导才会带来改变,防艾是就病讲病还是脱离不开权利话语。在全球基金要冻结对华援助的时候,关于政府和民间组织资金分配的问题成了核心议题,政府认为民间组织能力有问题,可是在有问题的培训下所获得的能力缺失,是社会学家默顿所总结的“训练的无能”(trained incapacity)。
只关注发放安全套,而少有关注有关安全套的公共政策,部分的原因来自于现代性所带来的所谓高效率科学化的“数目字管理”,小组疲于应付发套的数量,抽血检测的数量,由此才可以拿到项目,而公共政策的倡导没有办法数量化,何况一直以来,立法和公共政策的公众参与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很可惜,反而是一些安全套生产企业在身体力行地推动安全套广告的正当化,在这个过程中,很少看到防艾组织的身影。
是只满足于发放安全套还是倡导安全套公共政策的改变?是只满足于做“办事员”,还是同时做“公共政策的倡导者”?这直接跟防艾活动的定位有关系:是满足于艾滋防治的纯医学化还是综合的社会议题?是政府本位还是以易感人群为本位?
不是等这些问题有答案了才遵照实行,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全在于各种力量以切身行动来做出回答。
编辑推荐
- 万博体育app官网
- 万博体育app彩票靠谱
- 2025香港亚洲成人博览AsiaAdultExpo展后报道
- 2025柏林国际成人展圆满落幕,创新趋势引爆全场
- 2025广州国际性文化博览会圆满闭幕,引领情趣风潮!
- 比利时举办情趣玩具寻宝活动:一场颂扬情爱与健康的别样庆典
- 新万博赢钱技巧
- 李宏·说:未来的情趣器具陪伴
- 说唱歌手“侃爷”希望以妻子身体为原型推出情趣玩具
- 美国情趣用品商家积极应对特朗普关税贸易战,守住初心不断向前
相关资讯
- 1月 2026拉斯维加斯成人展
- 3月 2026巴西成人展
- 4月 万博体育appios
- 4月 万博体育app客户端下载
- 5月 万博体育app卡的进不去
- 2026年5月27日(水)~29日(金) 2026日本情趣展
- 8月 2026亚洲成人博览_香港
- 9月 万博体育app
- 9月 2026阿姆斯特丹成人展
- 10月 2026德国柏林成人展
相关产品推荐
更多- 狗万取款密码忘了
- 新年首展2026美国拉斯维加斯成人展ANVShow精彩集锦(2)
- 新年首展2026美国拉斯维加斯成人展ANVShow精彩集锦
- manbetx官网手机登陆放假通知,恭祝各位老板新春大吉财源广进!
- 把搞颜色做成正经生意,Lovehoney在公司设立自我羞羞室
- 告别“心机”标签,拥抱标准未来:外用延时行业迈入规范化发展新纪元
- 情趣玩具、SM狂欢!性感电影《我想要你》激情炸场圣丹斯
- 狗万返水
- 万博体育app苹果版
- 狗万返水几十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