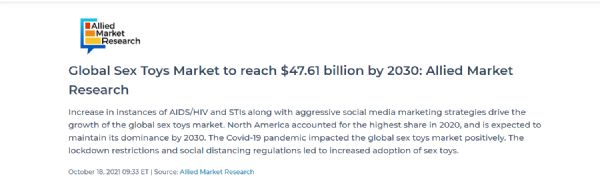性玩具非低级趣味:中国成人用品销售额超千亿
2009/9/28 10:24:09
核心提示:成人性用品即成人的玩具。据统计,我国现有性保健用品及相关生产企业一千多家,中国成人用品销售额超千亿。两性问题专家方刚说:如果我们认同性是基于娱乐目的的,并且认同娱乐是主要目的和手段,那么所有的性玩具,它从观念上应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也都是一个好的东西。
小朋友有小朋友的玩具,天经地义;大朋友拥有“大朋友的玩具”,却有“淫”还是“乐”之辩。
争辩是争辩,这丝毫未能妨碍中国性玩具用品(常冠以“性保健用品”之名)的蓬勃发展。有研究者统计:我国现有性保健用品及相关生产企业一千多家,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国家,多为出口,而国内近三分之一的进口洋货,原产地是在中国。出口创汇平均每年递增速度超过20%—这是指的生产。经营方面,全国目前有二十万家以上性用品的专卖店,中国性保健产业年销售额已经超过1000亿人民币—这个数据与我们印象当中,街头巷子里局促、隐蔽的“成人用品商店”的形象的确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在中国,“成人性玩具用品”的买卖仍属一个极为低调、隐秘的行业。
“短短的平头、大方框眼镜加上淡漠不羁的神情,使33岁的他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坐在性教育课堂末排的青涩少年。”这是美国《时代》周刊对温州爱侣公司总经理吴伟的一段描述,这个据说是“性保健品国内市场份额已占到了70%”的公司的老板也只有面对国外媒体时,才敢大胆地推销他的观念:人需要性玩具,就像口渴了需要喝水一样平常。
而在中国本土,吴伟和他的集研发、生产、经销渠道以及终端销售“一条龙”的家族极少在媒体露面,我们的数次约访,也一再遭到他们的婉言谢绝。
幸好,我们找到了开设有一百多家成人玩具连锁店的欢喜堂,老板粟卫国有着15年的从业经验,手握十大品牌、5000多款性用品的独家经营权。因为有着“中国保健协会惟一重点支持的成人用品连锁机构”的倚靠,粟卫国言辞大胆,有问必答,但我们也发现,他开设的一些社区店,平日挂着“XX街道计划生育服务办公室”的牌子,“一有领导来街道办检查工作,公司就把大门紧闭”。
而作为销售当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成人用品电子商城”,“北京桔色科技有限公司”强调:“我们就是一家普通的电子商务公司,”但这家“普通”的电子商务公司在创业初(正是电子商务最火暴的时期),却遭遇了“应聘者众,闻之色变,掉头就走”的尴尬。而其首席运营官在接受采访时,也有意识地说了句:“我们虽然出售成人玩具,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很开放……不意味着我们自己都会使用—那不乱套了吗?!”
而那些购买“性玩具”的顾客呢?“进来不说是给自己买,大多说给朋友买。买完东西,有些人连找的零钱都来不及接,便匆匆离去。”
消费者的“性趣”和产品带来不菲的利润让“性玩具”产业趋之若骛,但众人却又小心地与“性玩具”保持着距离,希图保留“清誉”。“书中有教条,身穿布衣裳”的人们着实有趣。
在中国汉语当中,“淫”解释为“过头”之意。然而,性欲望无可量化,当“性玩具”作为“性能力不足”的一个补充时,被认为无可指摘,但何谓“不足”?而恰恰人的欲望又没有穷尽,何又谓“过头”呢?
就在这种无法判别中,“性玩具”即成为了传统观念中的“淫具”。
女性主义学者葛尔·罗宾曾提出过一个性等级理论。她认为,性至少分成三个等级:好的性、坏的性、有争议的性。好的性被限制在婚姻之内,以生殖为目的,一夫一妻;坏的性指跨代级、同性恋、商业的,或者是人和动物,或者SM等;而中间存在一些很难区分、有争议的性,就比如性玩具。
而随着不同时代文化的变化、人们对性行为多元化的尊重,一些原本很难区分的“坏的性”和“有争议的性”有可能朝着更高等级过渡。
如果说,一部《断臂山》,让现在的同性恋越来越能被接纳为“有争议的性”(甚至“好的性”)的话。那么,“性玩具”这一“淫具”是否有从“争议的性(甚至是坏的性)”过渡到“好的性”的机会?
两性问题专家方刚说:如果我们认同性是基于娱乐目的的,并且认同娱乐是主要目的和手段,那么所有的性玩具,它从观念上应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也都是一个好的东西。
江晓原访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江晓原没有直接回答,他笑了笑:性玩具的“淫乐之辩”或许会出现在书本上,可是不大可能出现在床上。
编辑推荐
- 万博体育app官网
- 万博体育app彩票靠谱
- 2025香港亚洲成人博览AsiaAdultExpo展后报道
- 2025柏林国际成人展圆满落幕,创新趋势引爆全场
- 2025广州国际性文化博览会圆满闭幕,引领情趣风潮!
- 比利时举办情趣玩具寻宝活动:一场颂扬情爱与健康的别样庆典
- 新万博赢钱技巧
- 李宏·说:未来的情趣器具陪伴
- 说唱歌手“侃爷”希望以妻子身体为原型推出情趣玩具
- 美国情趣用品商家积极应对特朗普关税贸易战,守住初心不断向前
相关资讯
- 1月 2026拉斯维加斯成人展
- 3月 2026巴西成人展
- 4月 万博体育appios
- 4月 万博体育app客户端下载
- 5月 万博体育app卡的进不去
- 2026年5月27日(水)~29日(金) 2026日本情趣展
- 8月 2026亚洲成人博览_香港
- 9月 万博体育app
- 9月 2026阿姆斯特丹成人展
- 10月 2026德国柏林成人展
相关产品推荐
更多- 狗万取款密码忘了
- 新年首展2026美国拉斯维加斯成人展ANVShow精彩集锦(2)
- 新年首展2026美国拉斯维加斯成人展ANVShow精彩集锦
- manbetx官网手机登陆放假通知,恭祝各位老板新春大吉财源广进!
- 把搞颜色做成正经生意,Lovehoney在公司设立自我羞羞室
- 告别“心机”标签,拥抱标准未来:外用延时行业迈入规范化发展新纪元
- 情趣玩具、SM狂欢!性感电影《我想要你》激情炸场圣丹斯
- 狗万返水
- 万博体育app苹果版
- 狗万返水几十什么意思